被數位資本主義的巨輪輾過
當演算法成為新時代的摩洛克¶
每天早晨,我們從手機的推播通知中醒來。滑開螢幕的那一刻,就像是向古老的摩洛克神祇獻祭——我們把注意力、情感、甚至是思考能力,一點一滴地餵養給那些隱身在雲端的演算法。這不是誇張的比喻,而是當代生活的真實寫照。
十七世紀的哲學家法蘭西斯·培根曾經相信「知識即力量」,他以為透過理性思考,人類可以克服認知偏見,獲得真正的智慧。但今天,知識確實成了力量,卻不是我們每個人都能掌握的力量。相反地,少數科技巨頭壟斷了這種力量,將培根所說的「四種假象」——那些妨礙我們理性思考的錯誤傾向——轉化成精密的操控工具。

A distorted, glitch-art depiction of a figure resembling Moloch, symbolizing the unsettling power of AI and algorithmic systems.
被放大的偏見與被操控的選擇¶
想想看,當你在社群媒體上看到某則貼文時,演算法早就知道什麼內容會讓你停下來、什麼會讓你按讚、什麼會讓你分享。它利用的,正是培根所說的「種族假象」——人類天生傾向於相信符合自己期待的資訊。推薦系統不是在幫我們克服這種偏見,而是刻意地加深它,讓我們困在自己的資訊繭房裡。
這就像是《愛麗絲鏡中奇緣》裡的紅皇后告訴愛麗絲的話:「在這裡,妳得拼命地跑、不停地跑,才能保持在原位。」現代人就是這樣,必須不斷地適應演算法的變化、追逐平台的趨勢,僅僅是為了不被數位世界淘汰。所有的努力,最終只是為了站在原地。
而在這場永無止境的競賽中,我們逐漸失去了真正的自主性。每一個點擊、每一次滑動,都在訓練演算法更好地預測我們的行為。我們以為自己在做選擇,實際上卻是在被選擇。這種感受,讓人想起葡萄牙詩人佩索亞在《惶然錄》中描述的那種深刻的存在焦慮:「我什麼都不是。我將永遠什麼都不是。我不能指望成為什麼。但我在我內部有這世界的全部夢想。」

Alice and the Red Queen running, illustrating the "Red Queen's Race" metaphor.
數位時代的存在異化¶
佩索亞透過他的「異名者」創作,預示了數位時代自我身份的多重分裂。今天,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在不同的平台上維持不同的人格:在 LinkedIn 上是專業的工作者,在 Instagram 上是生活品味的展示者,在 X 上是觀點鮮明的評論家。這種分裂不再是藝術創作的技巧,而是數位生存的必要條件。
更深層的問題是,我們開始懷疑自己的真實性。當演算法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的喜好,當它能準確預測我們的行為,我們還能說自己是自由的嗎?這種「被透視」的感覺,讓現代人普遍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感——不是來自外在的壓迫,而是來自內在的被操控感。
監控資本主義的核心就在於此:它不再滿足於了解我們現在想要什麼,而是要預測和塑造我們未來的想要。這種「行為未來市場」的運作邏輯,讓培根「知識應當服務人類福祉」的理想完全變了調。知識確實成了力量,但這種力量不是解放我們,而是更精緻地控制我們。
在假象與真實之間尋找平衡¶
面對這樣的困境,我們既不能完全相信技術樂觀主義——認為更好的演算法設計或更嚴格的法規就能解決所有問題,也不能完全沉溺於存在主義的悲觀情緒中。真正的出路,可能在於認清這兩種視角的價值與限制。
培根的理性分析工具依然有用,它提醒我們識別演算法如何利用我們的認知偏見。當我們意識到推薦系統是如何運作的,當我們理解個人化廣告是如何鎖定我們的,我們就有了抵抗的起點。同時,佩索亞式的存在洞察也很重要,它讓我們不會對技術解決方案抱持過度樂觀的期待,認清數位時代的異化可能是現代性的深層結構問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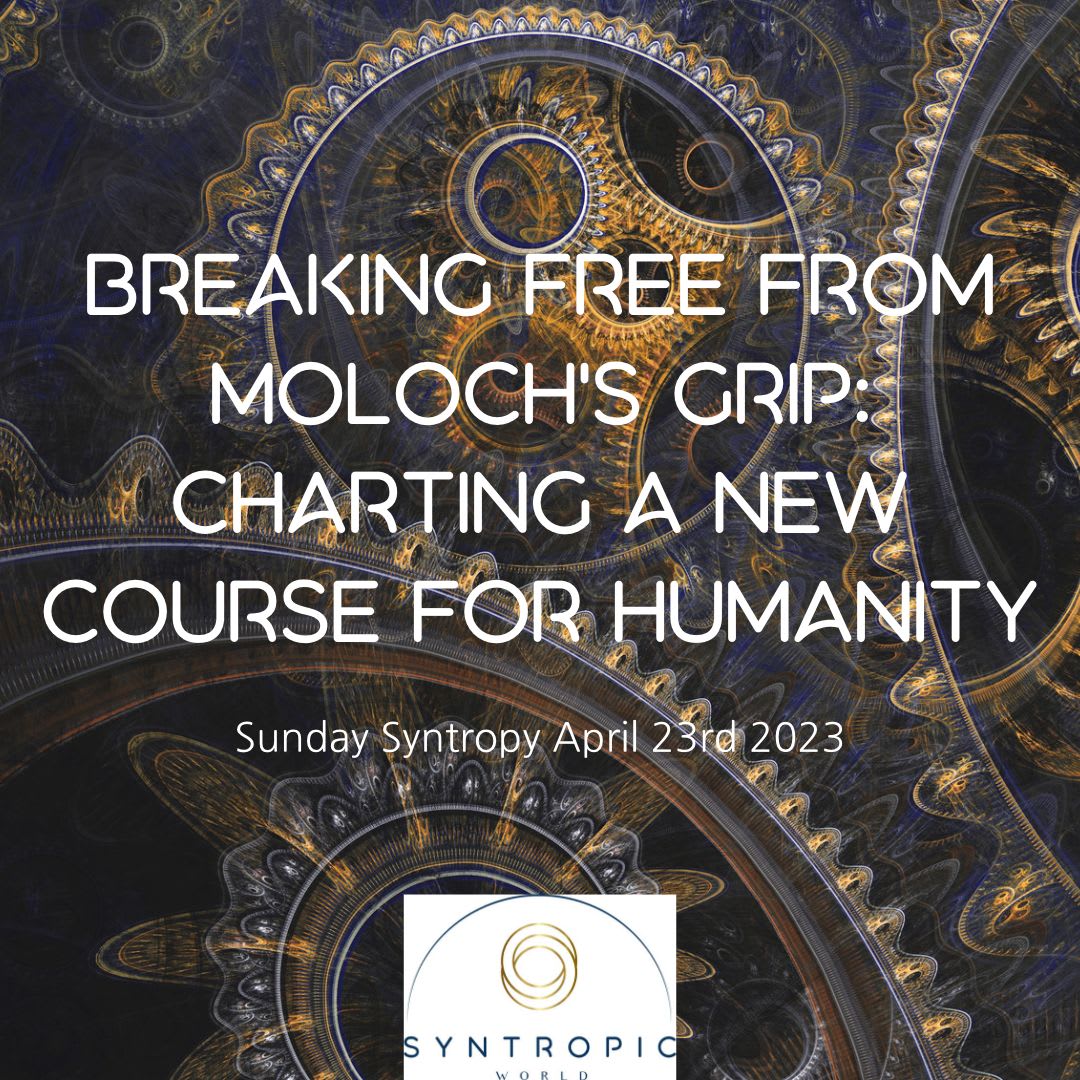
A graphic titled "Breaking Free From Moloch's Grip" overlays an intricate background of gears, suggesting complex systems.
在摩洛克的陰影中保持人性¶
最終,在這個被演算法包圍的時代,我們需要的是一種「辯證的清醒」。既要保持改變現狀的行動意志,也要承認改變的限度;既要運用理性工具分析和抵抗操控,也要在存在的深度中尋找不被任何外在力量完全征服的人性內核。
這不是要我們拒絕科技,而是要我們保持警覺。當我們下次打開手機、滑動螢幕時,記住自己還有選擇的權利——選擇不被演算法完全定義,選擇在數位的洪流中保持一點真實的自我。
因為在摩洛克的陰影中,最珍貴的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,而是那一點微弱但頑強的人性微光。